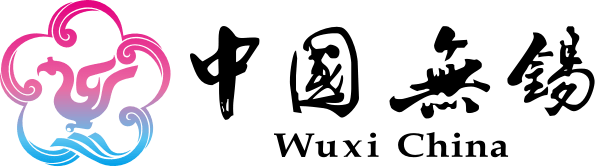天韵社的前身是无锡曲局。无锡曲局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而无锡人唱昆曲历史则与昆曲诞生几乎是同时的,无锡人唱昆曲的水平之高、之正宗,古人历代都有定评。——
如:明代万历年间的潘之恒的《鸾啸小品》卷三《曲派》:
“无锡宗魏而艳新声,陈奉萱、潘少泾为其晚劲者。”
“尝为曰:锡头昆尾吴为腹,缓急抑扬断复续。”——
这里特别指出“宗魏”,说明无锡人的曲唱,是魏良辅嫡传,最忠实的继承者之一。而“锡头”,即指吐字时,以无锡特色的声母为起音(无锡方言,咬字的喷口往往重于别的方言)。——
明代还有一句谚语广为流传:“船过梁溪莫唱曲”。《江苏戏曲·无锡卷》记了一则传说:楼船已过望亭,前面就是无锡,我们不要唱了。——
明末无锡流向京城的昆曲演员则被称为“锡山老国工”。
明代史玄《旧京遗事》记录:
常州无锡邹氏梨园,二十年旧有名吴下,主人亡后,子弟星散,今田皇亲家伶生、净,犹是锡山老国工也。——
明清时期,无锡风格的曲唱已被称为“无锡唱口”,并尊为“梁溪风范”。孔尚任的《桃花扇·选优》:
“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
意思就是曲唱以无锡唱口为标准。
清康熙九年,在寄畅园的一次曲会中,园主人秦松龄带领家乐歌者六七人,各抱乐器,衣着朴素,“恂恂如书生,列坐文石”,只一开口便“行云不流,万籁俱寂”,散文家兼词曲家金陵余怀叹道:
“盖度曲之工始于玉峰而盛于梁溪殆将百年矣,此道不绝如 线。”“良辅之道终盛于梁溪”。
小铁笛道人写于嘉庆年间的《日下看花记》称赞一位昆曲伶人,名叫何声明:
“周规折矩,音律精细,恪守梁溪风范,后学允堪奉为圭臬。”还评论他:“苦心孤诣,寂寂无闻,不亦难乎?何郎平素与同班讲习外,不妄交一人,衣帽朴素无华,安分自守,泊如也。”
这正是无锡曲人的典型风格。
以上,令我们看到了明清时期昆曲在无锡欣欣向荣的生态,它是滋生出“无锡曲局”的土壤。
无锡曲局从明末初创到民国九年迁入公园,这三百年间,曲友们前赴后继的艺术深耕和代际传承,成就了无锡清曲的根深叶茂。
清道光年间开始有了人员确凿的传承谱系。
老曲师吴畹卿名吴曾祺,以字行,从光绪年开始主持无锡曲局、天韵社长达50年之久。他精研曲韵,有理论有实践,擅唱能奏,近80岁演唱时,隔墙听之犹如“雏莺娇娃”。他精通各类器乐伴奏,尤擅琵琶三弦,是华秋萍的再传弟子。他教学严格,对字的“出音收韵”特别讲究,在他的手抄曲谱里,每个字都标上了归韵符号。几十年主持曲社活动中,培养了大批昆曲精英,其中有北京大学昆曲教师赵子敬,北上前先来无锡跟畹卿老曲师学习曲韵半年。赵子敬逝世后,他的昆曲弟子袁寒云写祭文载天津《晶报》,其中有:“子敬死,江南曲家唯畹老一人而已。”
天韵社除了吴畹卿,还有一大批高手,杨荫浏曾在《锡报》上连载《天韵杂谭》,根据老曲们的描述,记录了前辈鼓师陆振声、李紫霞、张敏斋,三弦手蒋旸谷、笛师陈馥亭,以及同时期的范鸣琴、沈养卿、乐述仙、李静轩其人其事其艺。其中最有趣的,一是陈馥亭弄笛,
“自有尺寸,丝毫不紊,时或唱者偶有错误,或偶有过速过迟之病,三弦鼓板均随之下矣,而馥亭方严正腔调,缓缓而来,虽错误至三、四拍之长,馥亭不为乱,亦不肯稍为迁就也。”
二是南派鼓师陆振声,说他击鼓板:
“出神入化,晚岁更精,趋于恬静之境”,“记曲极熟,鼻常夹眼镜,唱者有一字错落,则白眼由眼镜上出。”
杨荫浏先生12岁入无锡曲局跟随老曲师吴畹卿习昆曲及伴奏乐器,到吴畹卿1927年初去世,共15年,杨荫浏学会《天韵社曲谱》中九十套昆曲,“每套都背得很熟。”同时向吴畹卿学习琵琶,三弦。吴畹卿教学生特别严格,教琵琶时,先教小套,再教大套,如果前一套没弹好,是绝不教下一套的。1927年1月,吴畹卿去世,去世前,把自己收藏的全部乐谱及有关戏曲音乐文献、一把紫檀三弦,全部遗赠给杨荫浏,成为日后杨荫浏从事中国古典音乐研究的一份珍宝。这批珍宝,也许是无锡曲局内部代代相传的音乐遗产,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1922年,是天韵社对外交流活动最频繁的一个年份。
这年3月,上海苏州的俞粟庐、穆藕初、项馨吾等一行十几人来到无锡,与天韵社在公花园里“大世界”举行会唱。
8月,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指挥、首席小提琴家爱希汉姆经人介绍来到无锡考察中国音乐,吴畹卿为他组织了七个晚上的音乐会,全面展示了天韵社的各类音乐。丰富的有特色的音乐把爱希汉姆震服了,他写文章发表在当月的英文报纸《大陆报》上,说”所遇音乐团体,天韵社见称第一。“ 不仅如此,他离开中国后前往印度继续考察,此时已是12月,却写信给吴畹卿,说是”绕梁之音,未能暂忘,决请其夫人与女公子在印度暂待,孑然遄返“,电报刚到,人已在途,于是回到无锡和天韵社盘桓数日,最后那天正下着雪珠,他下午听了十番锣鼓,晚上七点登上火车,又回印度去了。临走还谆谆嘱咐要对这种音乐加以研究推广,让世界都能欣赏到。
同年的10月,苏州寄闲曲社到无锡访问天韵社并会唱,11月,无锡天韵社到苏州回访并会唱。
1929年无锡天韵社还和宜兴的协和社交流联谊,发现宜兴昆曲是当时唯一与无锡同宗同派的。为此两社来往更加亲密。
天韵社的活动,除了日常习曲、对外交流活动外,还有各种乘兴出游。1926年农历七月半,天韵社沈养卿、唐石琴、许寄萍、乐述先、李显臣、杨荫溥、杨荫浏七人相约买舟游湖:
“左抱琴,右挟管,买鱼沽酒”,“舟曲折经内河入湖,水光近挹,山色遥迎,浅芦丛中,渔歌酬答;群鸥起处,帆影徐来,对此一幅天然画图,不觉万虑皆消,于是相与披襟酌酒,和笛高歌,唱《三醉》一阙,余音未尽,飘然欲仙,几自忘其尚在人间世。”
“饮罢而歌,歌倦而饮,不觉万顷堂已在望矣。于是登堂稍休,放一叶扁舟,荡漾中流。”
至鼋头渚,“摄衣登岸,微风动处,第觉一阵清香……盍迹之,不数武,果见一塘粉荷,杂夹莲蓬丛中,掩映夕阳,弥益娇艳,余曰是不可以不赏,盍同歌一曲《赏荷》乎?于是沈子吹笛、李子作歌,众和之。兴尽,始循曲径上,……更循径登长生未央之馆,推窗一望,天水不分,背山面湖,别饶胜景,听渔歌樵唱,和以一曲《合仙》,不知仙人岛三万清凉界里,亦有此天趣否?”
“谈笑杂作,豪兴渐来,直至倦鸟投林,始徐徐放舟归,一轮明月,渐透林稍,大地湖山,顿成银世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曲友们纷纷撤往上海、云南、重庆等地,天韵社活动被迫中断。
1948年,在杨荫浏等人的筹划下,天韵社在公花园原址复社,并推举社内最为老成的前辈,鼓师范鸣琴任社长。但是好景不长,解放后,这些”封建残余“例被打倒,当然也不可能在公花园有公开活动了。但是,劫后余生的老社员们私下里还是有聚会的,老无锡城圈不大,他们住得都很近,常常晚饭后就踱到青果巷沈养卿老宅子”耕兰草堂“里,他家有个园子,种着兰草。他们聚到一起,往往先唱几段京戏,遮遮门面,然后就一支接一支唱昆曲,这些人里有范鸣琴、沈养卿、沈白涛、阚献之、蔡君植、诸健秋、唐慕尧、沈达中等。杨荫浏寒暑假总要回无锡,回来则必定要曲聚一番。1962年元旦他们在耕兰草堂曲聚时,杨荫浏唱了《斩窦》,此时的天韵社社员只剩下数位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中国迎来了料峭春寒,这一年,小岗村村民秘密押手印推动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制, 而在北京的中国音乐研究所,杨荫浏在抓紧他生命最后的几年,紧锣密鼓完善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为了其中一个鼓板的样子,他专门写信到无锡,询问老社员的情况,当他得知还有老社员健在时,兴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这个时候,曹安和先生则在研究生班开设了她生命中最后一期昆曲课,按古老的天韵社的教曲方法,向学生们传授“书房派”文人清曲。孙玄龄当时已经是杨荫浏助手了,所里因为他有昆曲基础,让他也去听课。这一听,就喜欢上了曹安和先生教的天韵社清曲,并跟随曹先生拍曲8年,为她录下了音,留下了至为宝贵的天韵社清曲遗产。
杨先生去世二十九年、曹先生去世的九年后,即2013年12月,无锡天韵社在古老的梁溪河畔复社了。无锡天韵社的复社最早是由苏州大学的周秦教授和原生态昆曲的捍卫者顾笃璜先生共同推动的;我市文化界领导如无锡文广新局、文联、广电集团 、锡剧院以及市地税局的领导都给予了关心支持,复社第二天《无锡日报》《江南晚报》《无锡商报》和广播电台、电视台都登载、播报了这条新闻。
“栽下梧桐引凤栖”, 2014年,杨荫浏先生的关门弟子、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田青老师一行人专程来访无锡天韵社,并提供了曹安和昆曲弟子孙玄龄先生的通讯方式。听闻此消息的孙玄龄先生十分高兴,2015、2016连续两年专程欣然来到无锡,将《天韵社曲谱》、杨荫浏先生的曲笛捐赠给新天韵社,并作相关讲座、教授天韵社清曲。已沉寂了数十年的天韵社清曲终于有了复活的希望。2016年,复社后的天韵社在北京首次唱响天韵社清曲,2019年,天韵社再次赴北京演唱,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古老的天韵社清曲复苏了。
无锡天韵社的百年坎坷,起起伏伏,屡断屡续,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命运是“同频共振”的。 天韵社的存在,不仅对于无锡有着保留乡土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全中国来说,它有着传统雅乐正声“活标本”的意义。